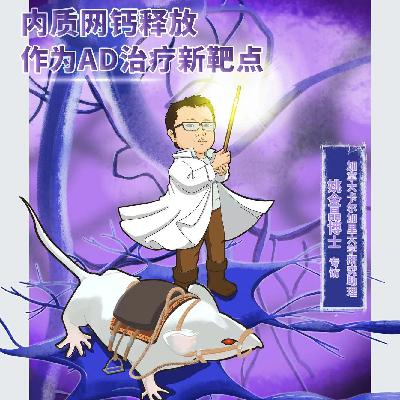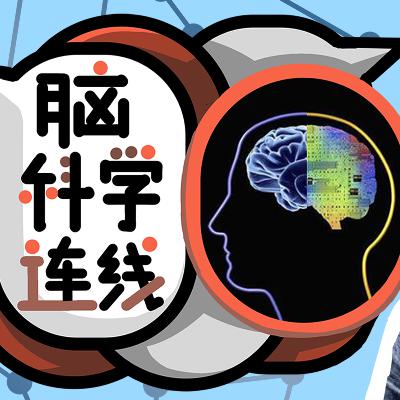专访 | 东京大学神经智能国际研究中心 蔡明博老师
Description
个人简历:
2004-2008年,北京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心理学双学士学位。
2009 - 2015年,美国贝勒医学院神经科学博士(导师:David M. Eagleman,副导师:Wei Ji Ma)
2015 - 201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导师:Yael Niv,合作者:Jonathan W. Pillow)
2019年至今,东京大学神经智能国际研究中心(IRCN)PI和项目助理教授
时间轴:
01:15 一、关于科研经历的简要介绍
04:16 二、关于时间感知的讨论
12:26 三、关于神经表征和学习本质的讨论
22:59 四、关于计算精神病学的讨论
31:55 五、关于留日任教的讨论
36:15 六、关于大卫·伊格曼的讨论
43:04 尾声:对我们听众朋友的建议
一、关于科研经历的简要介绍
主持人: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脑科学连线,我是主持人鸽子,本期节目呢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东京大学神经智能国际研究中心的蔡明博老师,那蔡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蔡明博:鸽子你好啊,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这次机会跟大家来交流,也祝大家伙好。
主持人:蔡老师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研究经历和现在做的方向吗?
蔡明博:那我从本科开始讲吧,我在大三还在一个研究纳米的实验室做一些比较跟电子有关的项目。后来因为学习心理学以后,对脑科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在本科毕设的时候做了一个跟脑成像的数据分析算法有关的毕业设计项目。
之后在博士期间在贝勒医学院,跟David Eagleman研究时间知觉。在这个期间,因为同时跟其他老师的学习,对贝叶斯推断和一些其他方向慢慢产生兴趣,所以在我博士后阶段,就进入普林斯顿的Yael Niv实验室,相当于在研究方向上有一定的转变。之后更加关注于人的学习,另一方面又回到了脑成像算法的开发上面。当然之所以会关注脑成像算法开发,其实是因为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发现了一些算法中存在的问题,于是发现所学的那些统计学的贝叶斯的方法可以用来开发更好的算法。就相当于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博士后之后,我在东京大学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方向上也有了一些扩展,一方面我们还是在研究人们是怎么样进行学习,比如如何学习可以获得更好的奖赏。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对精神疾病能产生帮助。另外,我们继续还是在做脑成像分析的一些算法。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借鉴心理学,尤其是在发展心理学得到的一些关于儿童或者婴儿怎么样学习的启发来设计一些新的神经网络,让它能够学到我们认为婴儿在一定的阶段可能已经掌握的一些能力。最后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方向是,怎么样可以用脑成像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自发的思维。
《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二、关于时间感知的讨论
主持人:那我们就先从最开始您那个博士阶段的研究说起,是关于时间感知的。因为我感觉时间这个话题其实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因为就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同样一段时间,如果我这一周我的工作。非常的多,很忙,接收到的信息量大。就感觉这周特别的漫长,这可能就是一个所谓从个人主观而言的时间感知的一个不稳定性和差异性。所以蔡老师之前他关注的是视觉刺激和人的时间感知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您可以简单的为我们科普一下,在这个研究当中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或者说您的一些研究方法?
蔡明博: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研究时间知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对时间的感知或者说判断其实有不同尺度的。通常情况下,学者大概会划分出三个尺度来研究。一个是在秒以下的时间尺度,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精确的时间范围。下一个时间尺度是我们往往更加有意识、会关注到的时间尺度,就是在几秒甚至或者几分钟这时间尺度。这个时间尺度就可能更加涉及到你生活当中等班车啊或者等地铁时候这样的时间的感知。那么还有更长的时间尺度,就会涉及到生物的节律,其实在这个尺度上我们可能不一定把它叫感知。在这个尺度上可能更多还是生物学研究会多一些。
我在博士阶段其实更加关注于比较短的时间尺度。在这个大的领域,学者们发现其实人的时间感知往往是很不确定的,而且是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换言之,我们其实很难有非常精确的对时间的判断。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多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事情是先发生,什么事情是后发生。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时间的先后判断。对时间先后判断有什么用呢?很重要一个用处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因果推断。你怎么知道两个事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那其实需要根据各种方面的因素来推断,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时间先后:你会认为如果一个事情是原因的话,那它应该在结果之前发生。可是实际上我们对事件的时间先后的判断,还真的可以发生改变。比如说,假设现在给你一个实验,在你每次移动鼠标或者在点击鼠标的时候,我都让屏幕上显示出对应的变化。但是我让光标的移动和你点鼠标之后这个电脑的反应都有个延迟,举例来说我可能给你一百毫秒的延迟。我让你适应了一段这个延迟,比如适应了一分钟甚至半分钟之后,突然让这个电脑给你一些正常的反馈,比如说你点一下鼠标我马上呈现一些图片,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在你点鼠标之后立即呈现的视觉刺激会被你判断成在你点鼠标之前发生,也就说你对这个时间的先后判断,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颠倒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当时认为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可能是在不同的modality(通道)分别进行的,比如说你可以认为听觉是一个通道,视觉是一个通道,自己的运动也可以当作另一个通道。可能我们在每个通道之内会保持一个大概的时间判断。但是不同通道得到的时间信息未必同步。随着身体的成长和环境的变化,任何两个通道获得的时间信号之间的物理延迟都可能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我们的大脑根据不同通道间延迟的变化不断调整。正是因为这种调整的机制使得我们有前面提到的误判。
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关注什么样的刺激可以影响人的对时间长短的判断,以及如果两个视觉刺激给你不同的关于时间长短的信息,人脑是怎么整合这样的信息的。当时心理学界有一个非常火的思潮,就是说人脑可能在做很多推断的时候,都会以接近于贝叶斯的方式来整合。我想知道人在处理时间信息有冲突的刺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用贝叶斯的方式来整合?但最后发现其实也不完全是。它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给被试呈现的刺激是不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呈现的刺激相对来说是一种在心理学实验常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常见的实验刺激。当大脑面对这样的刺激的时候,整合的方式并不是像贝叶斯那样最优的。
主持人:所以这些研究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它就能够用您这个研究当中的某个结论来去解释呢?什么样特别的视觉刺激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这种时间误判?
蔡明博:我们发现如果你重复观察一个实验刺激,你会觉得它所呈现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如果你已经习惯于做一件事情,可能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如果今天有很多新的事情发生,也许你会觉得今天好像更充实,发生更多的事情,似乎时间变长了。这两个现象有可能有关联,但是确实它们是在两个不同时间尺度上发生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说这两个是同一个机制,但至少它们在现象上非常接近。
三、关于神经表征和学习本质
主持人:就刚才您提到说视觉刺激的研究,是不是还需要去看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怎么表征的?这个方面在您的领域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有没有一些核心的问题呢?
蔡明博: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博士后阶段选择转换研究方向的原因。在我的博士期间经常会参加视觉科学领域的会议。视觉科学家最重视的问题就是神经系统是怎么表征视觉输入的。在我们跟世界交互的时候,我们心里所体会到的世界是三维的。而我们的脑子接受的是来源于每个像素的信息,可以认为是二维的图片,我们的脑子能够最终把它分割成各个不同的物体、建立了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空间的表征。通常视觉科学家把从视觉输入到最后形成的这些表征之间的表征称为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但是对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我们是一直不理解的:它们到底是在编码什么样的信息,应该怎样研究这些表征。那我们一旦讨论到在编码什么,就会想问编码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在视觉领域的人通常会觉得,编码是为了更好的表征环境的本质。那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因为从人和环境交互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很难真正的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如果从机器学习的角度可能可以更好地理解我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给你标注你眼前看到的图片,说这个眼前就是一个人,你把这个标注当成一个ground truth的话,那一个机器学习系统可以学习对眼前的图片说我看到这个图片这里有个人。可是这样的标注其实对人来说从来几乎没有,或者说即使有也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而婴儿却自己可以慢慢地发现周围有哪些玩具,哪些玩具可以去玩。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婴儿说,眼前这些像素点其实应该组合在一起被当成一个物体,那些像素点可以当成另一个物体,所谓的ground truth对于大脑来学习分割环境成物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任务来说其实是没有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假设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