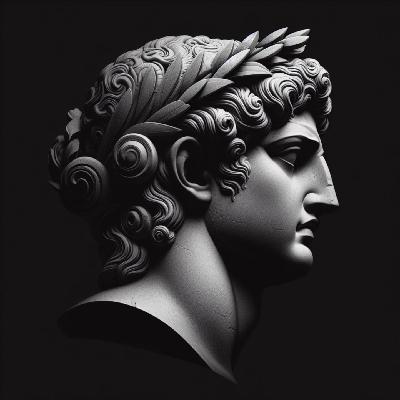读资治通鉴:桓玄篡逆,何以不敢不愿杀刘裕
Description
话说
当桓玄即将篡夺帝位之时,他举起了屠刀,开始清除北府军中那些不与自己同心的旧部将领。在此危局之下,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人,相继逃亡北方的燕国。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故国,投奔了异族,为后世那些投降北魏的刘昶、萧宝寅之流,开了一个不光彩的先例。
我们必须承认,这几位将领,也曾有自己的志向与操守,他们难道是从一开始就盘算着这种卑劣的逃亡之计,作为自己的退路吗?恐怕不是。他们只是在死亡的逼迫之下,仓皇失措,不暇选择而已。然而,他们最终落得一个进退失据、为人所不齿的下场,这终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面对桓玄的叛逆,这不仅仅是一个必须躲避的灾祸。即便灾祸暂时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一个有骨气的人,又怎能忍受向他屈服呢?他们本可以占据山阳,起兵讨伐桓玄。这一举动,即便不完全是出于对晋室的忠诚,也绝对是一个大丈夫应有的气节!可他们最终,为何会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要逃到鲜卑人的地盘去苟全性命呢?
然而,刘裕,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同样出身北府,也曾是刘牢之的部将,但他坦然自立于镇江京口,内心没有丝毫的畏惧。桓玄难道对刘裕没有猜忌吗?当然有。但刘裕拥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在他眼中,桓玄的威胁,尚不足以让自己忧虑。他返回京口,名义上是为了从长计议对付桓玄,但他却暂时将桓玄搁置一旁,转而雷厉风行,率军向东阳进击,击溃了卢循;随即又挥师挫败了徐道覆;并一路追击卢循至晋安,再次将其击败。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一天放松过自己的军事行动。
他所做的一切,名义上是为晋室,实际上却像是在为桓玄效力;而看似在为桓玄效力,其根本目的,却又是在巩固晋室的根基——同时,也是在巩固他自己的根基。他的威望在平叛中树立,他的军队在实战中磨砺。他仿佛根本不知道桓玄即将要篡位,而桓玄也因此无法揣测他的真实意图。不,这不仅仅是无法揣测,是即便揣测到了,也已无计可施。
因此,当桓玄的妻子刘氏劝他除掉刘裕时,桓玄只能无奈地回答:“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意思是 “我正要平定中原,非刘裕不可担当此任。”他一方面想要利用刘裕,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刘裕的威望已经建立,不再是自己能够轻易铲除的了。一个知道对方不可除去,只能隐忍厚待,以待时机;另一个也知道对方无法除掉自己,所以公然入朝,毫无疑惧。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刘裕三破妖贼,他所行的,是匡扶社稷的正道;他内心定力坚定。这使他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让旁人无可指摘,即便心存怀疑,也找不到任何名义来制裁他。刘裕,已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过来,这就是掌握了制衡桓玄的绝对主动权。
历史的经验,发人深省。
当一个士人,身处逆乱将起、国祚垂危、忧患接踵而至的时代,他该如何自处?一味地诡诈顺从,必将陷入不义的深渊;而急躁地投机冒进,则会迷失方向。唯一的正道,是首先去做那些自己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奠定宏大谋略、成就非凡事业的关键,正在于此;而保全自身、坚守节操,在乱世中不至颠沛流离的关键,也正在于此。
司马休之等人,正是因为放弃了自己本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即便他们内心怀有讨伐逆贼的志向,最终也只能堕入任人宰割的幽暗深谷。
英雄的谋略,君子应当从中汲取智慧:先求立身之安,而后伺机而动;先固人际之信,而后谋求发展。以正道而行之,运用此等智慧,便足以让一个人,在天纲断裂、地维崩坼的至暗时刻,依然能够昂然屹立,而无愧于心!